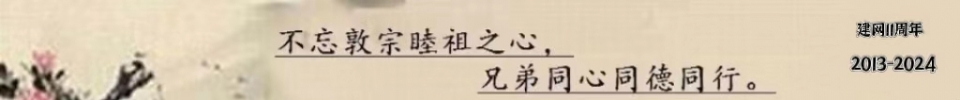胡明文学作品
换个心态看世界
作者:胡明
她的生活看起来似乎还不错,但事实上她却经常不快乐。她的先生虽然事业有成但经常出差,让她独守空房,提心吊胆;儿子虽然聪明伶俐,但经常在学校调皮捣蛋;婆婆虽然身体健康,但喜欢无事生非,三天两头找茬给她气受;在单位她是一个业绩平平的小职员,什么升职加薪的机会都轮不到她……她把痛苦向心理专家倾诉,心理专家说:“让我把你的倾诉倒过来看看如何——先生虽然经常出差在外,让你提心吊胆,独守空房,但是事业有成;儿子虽然经常在学校调皮捣蛋,但是聪明伶俐;婆婆虽然喜欢无事生非,三天两头找茬给点儿气受,但是身体健康;在单位虽然升职加薪的机会轮不到自己,作为一个小职员业绩平平,但是没有太大的压力,可以自由自在地观花开花落,望云卷云舒……这样看来,情况的确不错,是不是?”
专家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:
有一个老妇人,她生有两个女儿。大女儿嫁给一个染布的为妻,小女儿嫁给了一个卖伞的人,两家过得都不错。看着两个女儿丰衣足食,老妇人原本应该高兴才对,可是她却每日都很愁苦。因为,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,老妇人就为小女儿家的生意担忧:晴天有谁会去她那里买雨伞呢?而到了阴天的时候,她又开始为大女儿担心了,天气阴暗或者下雨了,她染出来的布无法晾晒真是糟透了!就这样,无论是刮风下雨,还是晴好的天气,她都在发愁,眼见得日渐消瘦。这一天,村里来了个智者,当他听老妇人讲完自己的境遇时,微笑着对老妇人说:“你为什么不倒过来看?晴天时,你的大女儿染坊生意一定好,而下雨的时候,小女儿家的雨伞生意就好。这样,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,你都有一个女儿在赚钱呢!”
无论是专家还是智者,他们都说了一句相同的话:倒过来看。
倒过来看其实就是换个心态看世界。同样半杯水,不同的心态会有不同的感觉,悲观的人说,我只有半杯水了,乐观的人说,我还有半杯水呢。
生活中我们总是放大痛苦,记住折磨,而忽略了幸福,忘记快乐。很多时候,换个心态看世界,就会发现,其实我们已经拥有很多。
云烟深处
作者:胡明
二十几年来,爷爷头戴一顶黑色的针织蒙一抹帽,穿一件粗布老棉袄,一直在镜框中,默默地看着我。
已近不惑的我,眼泪是越来越少了,是否已被岁月风干了呢?我不知道,只知道那张渐渐发黄泛白的照片,象秋风中一枚霜染的红叶,遥远地悬挂在云烟深处,每当心潮涌起,爷爷的笑容,便被薄纱似的雾气轻慢地打湿……
记忆中,爹娘总有忙不完的庄稼活,一年四季老在那几亩地里刨来刨去,很少有时间照顾我们,更多的时候,则是不耐烦地让我们这些碍手碍脚的小家伙走远点,别添乱——那是爷爷上姑姑家小住的日子。
爷爷在家的日子,我们是不寂寞的。在柔柔的阳光下,牵着他青筋密布的手到田野里看正拔节的庄稼;秋天和爷爷一起,上山薅茅草、龙须草,搓成光溜溜瓷实实的绳子捆秸杆,也会为找到挂满果的山里红而欢呼雀跃;冬天,拿着小玻璃瓶和两根削尖的细木棍,在爷爷的指点下,翻开阴暗角落的山石,看看有没有翘着尾巴的蝎子……。
在天气晴和的日子,拿着竹棍拍打爷爷晾晒的被褥也是我们的乐趣,看细细的灰尘在光影里四散逃逸,我们象打了大胜仗一样得意,坐在爷爷的怀里要战利品。爷爷在我们心目中,更多时候是和我们一起玩耍的伙伴。记得一个秋天,天气晴朗,我到前院找爷爷,爷爷把头天晚上换下来的粗布上衣递给我,让我捉衣服上的虱子,凑着窗棂透过的明媚的阳光,我仔细翻找,碰巧母亲来喊爷爷吃饭,仓促间爷爷赶紧拿走衣服藏到身后,象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般局促不安:原来爷爷也和我一样怕我娘啊!这个发现让我开心了许多日子。
农闲的时候,爷爷常常蹲在前院那棵老槐树下,笑眯眯地,握着那支一尺多长的大烟袋,一边和人们闲聊,一边有滋有味地咂摸如旱烟一般苦香的岁月。当初夏时分,米黄的槐花热热闹闹地挤在枝头,调皮的小鸟啄掉花瓣,轻轻飘落下来,我便在爷爷身后,欢喜地捏起落在他肩头的灿烂的槐花,放在手心里,紧紧握住再缓缓松开,凑近了去闻那清幽的香味。
在收获的季节,爷爷满是皱纹的脸整日象一朵盛开的大菊花,这是爷爷腰杆硬朗笑得响亮的季节。那连着庄稼地和家的小路,被祖祖辈辈穿着粗布鞋布满厚茧的脚,踩得明光光的,比城里的水泥路还光溜厚实,那是父老乡亲梦境里奔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啊!有多少人,就在这乡间小路无数的来回往复中,走完了一生长长的时光?
印象中唯一一次见到爷爷生气是在暑假期间,那年我有九岁了吧,梅雨季节刚刚过去,连天的暴雨,使大大小小的坑塘里,蓄满了积水,我和几个女孩子,只穿了一条裤衩,在村头一个大水塘里,狗刨般地扑腾。上游的水哗哗地淌过石挡子,源源不断地泄进水塘,满溢后又把玉米地冲出一道长长的口子,急急地向低洼处奔去。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,也不管前几天在大堰中捞出的男孩尸体是如何让大人恐怖,只管打着水仗。正开心间,爷爷就黑着脸站在挡子高大的青石板上,象一个威风凛凛的老将军:“你们不怕被淹死?上来!”他气咻咻地嚷,直到看着我们一个个上岸回家,才背着手到地里转悠去了。
最美好的时光应该是在冬天。放寒假的时候,爷爷一人住的三间土坯房内,堂屋总是燃着旺旺的炭火,我们兄妹搬几把小木椅,围坐在火盆边,看用爷爷给的零花钱买的连环画,看完了,就脱了厚笨的老棉靴,把脚伸在火边,暖烘烘的炭火把袜子烤出微烟,丝丝缕缕袅袅升腾。饿了,爷爷把过年蒸的包子(有白菜油馅儿的,还有肉馅儿的)埋在红红的灰烬里,隔一会儿,翻一下,烤得又焦又黄,吃到嘴里,外酥里嫩,香喷喷的(在现代生活中,微波炉的使用也许会让我们吃得更放心,但与爷爷那灰土土的烧烤比,却少了多少开心!)一个寒假就这样在暖烘烘香喷喷的感觉中飞逝而去。
十岁那年的春天,爷爷走过岗坡,坐了公共汽车,进城去了,去照看小叔家刚一岁的女儿,那年爷爷七十二岁。
不知是上学没有乐趣还是时光走得太慢,爷爷离开的日子,我总是怅怅的,像是丢了什么东西。放学后,假期时,我总爱静静地站在村边,期待岗坡上走下来那熟悉而苍老的身影。
两年后的一个秋夜,爷爷终于回来了,是被抬回来的。担架上的爷爷沉沉地睡着,脸像黄表纸一样。输液管里的液体缓缓地滴着,象我脸庞滑落的绝望的泪珠,而哥哥一直抱着爷爷的脚放在自己的胸前暖着,他的脚,象石头一样冰凉……当爷爷体内的血液象被堵塞了的水渠,慢慢回流到输液管内,年幼的我们,在深秋的暗夜里,第一次领略了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无常……
爷爷就躺在离家很近的麦田里,那片麦田,我们站在村头就能看见。但是,离我们很近很近的爷爷,如今是真的走远了,他不是上了岗坡,不是进了小城,而是一直走到了云烟深处。
那年的清明,有细细的雨若有若无的飘落。放学后的我没有回家,径直来到爷爷的坟前。那座坟,已经融入周围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坟包之中,坟头上一样的芳草萋萋。微风拂过,吹起坟前的火纸灰烬,纸灰散开来,象一只只黑色的蝴蝶,在低空轻轻翻飞。
而我,在斜风细雨中,就那样跪在爷爷的墓前,固执地相信,在头顶,那无穷高远的地方,一定还有一个世界,而爷爷就在那里,爱怜地看着孤独的我,在人间四月青青的麦田里,独自饮尽无数伤逝岁月……
先从脚上吃
作者:胡明
生活如一杯白开水,在慢慢的啜饮中,她和他度过了婚姻的第二个七年之痒。
象大多数没有故事的夫妻一样,日子波澜不惊地缓缓流淌。十几年来,她和他用微薄的工资收入一点点还清建房的欠款,侍奉八十高龄的婆母起居,供养十四岁的女儿上了高中。她没有一件金银首饰——虽然她曾经梦想,那怕是一枚小小的铂金耳钉,穿过早已打好了的耳孔,当她走在阳光下,脸颊旁的耳钉会灿烂地闪耀璀璨的光芒。然而,她没有。相比之下,他更实在地过日子,衣服只要不破烂,他就不让她给他买新的——半死不活的单位,五百多元的工资让他不得不对任何支出都精打细算。
她和他也有很多次争吵,却从未为钱的事不欢,虽然清贫也曾相伴着无眠,在许多暗夜里,让那张单薄的木板床轻轻低吟。当婚前的绮丽梦想在现实生活中,渐渐显得遥不可及,温情也象一缕轻烟,慢慢飘散在微风里。
岁月的画笔一点点染白他的头发,也在她的额头、眼梢描上浅浅的波纹。生活磨砺掉年轻的激情,她和他行走在秋天的落叶里。
那天,当她看到螳螂交配后雄螳螂会被雌螳螂吃掉的文章,问他:如果我们是两只螳螂,在我吃掉你时,你希望我先从哪里下口?他连想也没想,说:先从脚上。她有些失望,然后想,脚那么脏有什么好吃的!为什么不是嘴巴?先从嘴巴上吃——在热烈地亲吻中、在巅峰的交融中涅槃,难道不好吗?
她没有问他为什么这样回答,在她的感觉中,他不过是个不善言辞也不懂浪漫的实在人。这许多年来,她不止一次地为此感到遗憾,也不止一次地如此劝慰自己。
日子一天天走过,走过一个个无奈和清冷。一天早晨,她在整理他的记事本时发现了他写下的她的问话和他的回答:如果我们是两只螳螂,我希望我的爱人先从脚上开始吃我,好留下我的嘴巴和她多说一会儿话。
这天早晨的朝霞很美,象一只鹰伸展着绛紫色的翅膀,挥洒下一片光辉,暖暖的,给她脸庞滑落的泪珠镀上了铂金般璀璨的光芒。